藏着孩子不让探望,怎么办?
为提升家事案件审理效果、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自2019年4月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携手探索合作机制,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中委托阳光中心选派社工,开展家事调查、调解、心理疏导、回访观护、探望监督、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四年来,上海二中院少年家事庭的法官们与阳光中心的社工们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各类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身心健康、发展利益得到了全面保护。今起,我们将分享合作机制建立以来的典型案例。希望每一位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阴霾的孩子都能重新沐浴阳光,快乐成长。

案情
无法探望幼女 父亲诉至法院
小刚与茉莉都是80后,相识不久便迈入婚姻殿堂,并很快有了女儿妙妙。也许是因为闪婚闪育,夫妻双方感情基础并不牢固,两人在婚后争吵不断。在女儿5个月大时,茉莉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小刚也一口答应了茉莉的所有离婚条件,两人十分干脆地在法院的调解下离了婚,并约定妙妙随小刚共同生活。不料三个月后,茉莉以哺乳为由从小刚处抱走了妙妙,并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法院考虑到孩子仍在哺乳期,确实更需要母亲抚养,依法判决妙妙随茉莉共同生活。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茉莉的不配合,小刚没再见过女儿,两人还曾因此爆发肢体冲突。忍无可忍的小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每个月探望女儿半天、茉莉可全程陪同。茉莉则以孩子太小、不认识小刚为由,不同意小刚的探望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小刚的诉讼请求,茉莉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社工参与化解 父母达成协议
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二审合议庭委托阳光中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共同参与到本案的化解工作中,并分别与茉莉和小刚约谈。
对茉莉,主审法官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解释了小刚作为父亲所享有探望权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以及茉莉作为母亲所负有的配合义务;社工则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角度说明了父亲参与女儿生活、成长的必要性及种种益处。
对小刚,主审法官和社工结合女儿年仅两岁的实际情况和小刚相对“直男”的性格特点,就探望时如何与女儿接触、沟通给予指导。
为了帮助茉莉和小刚重建信任关系,主审法官和社工努力引导两人学会区分彼此间的关系问题与两人在女儿抚养上的关系问题,努力形成在女儿抚养问题上应相互合作的统一认识。
在社工的提议下,茉莉将手机中女儿的近照分享给了小刚。终于,对小刚的探望权,茉莉也松了口,但希望探望时有法院工作人员陪同。
为了打消茉莉最后的顾虑,主审法官从《上海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意见》中找到依据,提议由社工作为探望监督人,协助监督后续探望权的行使。
最终,茉莉和小刚达成调解协议,同意由社工开展为期三个月、每月一次的探望监督。
协作
规范流程 分工合作
引导双方自主探望
为了规范开展监督工作,社工在主审法官的指导下作了精心的研究与准备。每次探望监督前,社工都会和小刚、茉莉联系,就时间、地点、限定参与人员等内容进行约定。
第一次探望监督刚开始时,妙妙不仅对探望地点十分陌生,也对小刚表现得非常生疏。就在小刚不知所措的时候,社工介入其中,先陪伴孩子熟悉环境,再逐步指导小刚通过玩玩具、讲故事等方式与女儿互动。另一名社工则陪伴茉莉在一旁观察,缓解茉莉的焦虑情绪。
每次探望监督结束后,社工都邀请小刚与茉莉填写探望评测单,向社工反馈本次探望的感受,并就各自对后续自主协商探望的信心程度进行自评。
在三个月的探望监督结束之际,茉莉申请延长社工陪同探望监督的时间。经了解,是因为茉莉与小刚在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上仍存分歧,对小刚心存芥蒂而提出这一申请。考虑到夫妻财产分割与探望权无关,且孩子在探望监督中逐步表现出对小刚的熟悉与接纳,小刚也表现积极,与女儿的互动亲切自然,亲子关系趋于稳定,因此阳光中心未再延长探望监督的时间。结束这个案件的相关工作后,社工制作了探望监督工作报告并提交主审法官。
法官点评
《上海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共同协商确认探望监督人,由其协助探望权的正当行使。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指定和写明如探望权行使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与探望监督人联系。
探望监督人的人选可从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和当事人均认可的亲属中产生,并经由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定。探望监督人可在当事人后续探望中协助解决出现的争议问题,并可发挥观察协调、亲职教育等作用,发挥其专业知识、扎根基层等优势,第一时间帮助纠纷化解。
需要注意的是,探望权是在子女成年前非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都享有的法定权利。那么,是否意味着探望监督人就应该一直监督到子女成年呢?当然不是。本案中,二审法院委托青少年事务社工担任探望监督人以及社工在探望监督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做法,使探望监督人制度的目标更加明晰,即帮助当事人从监督下探望逐步过渡到自主合作完成探望,从而实现探望权纠纷的长效化解。本案中,社工围绕这一目标,运用社会工作领域的原则与工作思路开展探望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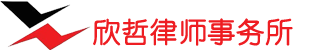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